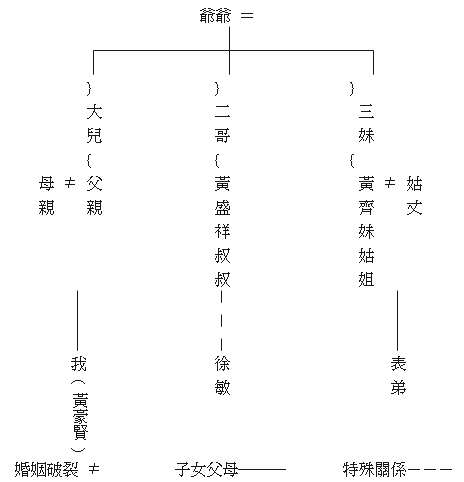|
王府井大街十三號 6A 黃豪賢 【故事提要】 故事講述一名香港青年人黃豪賢,為了完成父親遺願,將其骨灰送返北京安葬。期間,他領會到中國文化對社會有正負的影響,從而體會文化的重要性,盡顯當中的情。
人物關係表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二日——陰天。 我呆立在巨型玻璃幕牆旁,凝視從天際降下的雨粉。雨點灑在玻璃上凝聚成水珠,緩緩沿窗滑下。 「豪──」一把永世難忘的聲音破空而至,通過耳管直鑽進耳鼓裏,我先是遭雷殛般猛震一頓,遂激起心頭的蕩漾。 倘若時間能在這瞬間永遠停留的話,我會選擇永遠地背喚我的人。哼!不過這想法未免太過幼稚,人總要活在殘酷的現實嘛! 我深吸一口氣、緩緩摟轉身軀。入目的是個老頭兒躺在凌亂的被鋪上。一副陝長、臘黃、粗糙的臉孔予人飽歷風霜的感覺;兩邊骨高高聳起,配以一個筆直鼻子,極為好看;然而一雙充滿盼望的眸子緊緊盯進我眼內——這是我的父親。 父親二十來歲從北京偷渡來香港,三十歲左右結識母親。在他的甚麼「我會照顧你一生一世」的甜言蜜語下,純真的母親便下嫁給父親。 唉!又一個無知少女被騙倒。 因為父親是個標準的職業賭徒,可謂無賭不歡。母親從早到晚車衣得來的工資,均給父親一股腦兒輸掉,以致生活艱苦。在這樣惡劣的經濟環境下,我不爭氣的從母體鑽出。 黃豪賢不識時務出世了! 在我出世那年,母親曾打算離開我們,但在父親苦苦哀求下,又甚麼「對不起!我會戒賭,不要走!」我想這些話只有我蠢老母才相信,男人哪有永遠的承諾。結果媽足足等了這句話四年。 某一天,她對我說:「我走了。」 所以我痛恨父親,曾想過狠狠揍他一頓,但我明白這只是個遐想,根本不會實行,哈,至少直到現在也未試過。 母親走後,父親便沾上吸煙的壞習慣,早晚機械式般把一支又一支的香煙塞進口中,結果晚年患上末期肺癌,躺在這張病上。 父親微弱的聲音顫道:「咳……兒子,你可知爹畢生有兩件憾事?」 我不屑地斜掃他一眼。 父親把目光直勾勾地盯天花,頹然道:「咳……第一件事是關於你娘的。對不起!我沒給你媽幸福,我不是個好丈夫、好爸爸,我……咳……知錯了。請你原諒爹吧。」 荒謬!難道說了四年的同一句謊言也有人相信嗎?我倒沒像媽那麼笨! 我不忿地回應:「你認為一句話便可作出我和娘多年痛苦的補償嗎?」 父親沉甸甸地呼出一口大氣,眼泛淚光道……「咳咳,我是真心悔改的,我懇求你原諒我,請你給我一個機會好麼?咳!」片刻間,被鋪上多添了一潭赤紅的鮮血。 我大呼道:「醫生!病人出事了!」 人總是失去了才懂珍惜。不知怎的,我知道父親這次是真心悔改的…… 接張開懷有殘留血漬的小口道:「北京王府井大……街十三號,把我葬在那裏。」口中再噴出一蓬血雨。 「爸!」我竟喚了聲「爸」。 父親臉色開始轉灰,用殘餘的一口氣問道:「你原諒爹嗎?我走了……照顧娘。」 「爹!我甚麼也原諒!」我激動地回答。 父親微一點頭,慢慢蓋上眼簾。 「咇——」,心跳機停止運作,父親含笑而終,享年五十六歲。 二零零二年二月八日——晴天。 事隔半年,我捧父親骨灰乘飛機直抵北京——那是父親的故鄉。在起行之前,我已知會當地的叔叔,他今日黃昏於機場B大堂等待。 半年了,父親的噩耗對我的打擊漸漸淡化起來,看來時間真的能沖淡一切。 一位身材略胖、五官端正的中年男子老土地高舉「侄兒黃豪賢」的大字牌。果真搶眼!一看便知他是我的權叔,因為他與爹面貌像倒模機般製造出來,十分酷似。只不過額骨比爹闊了點,予人忠實的感覺。 瞥那高舉過頭的大字牌,我忍尷尬的笑容,用那半咸半淡的國語道:「祥叔叔,你好!我是你的侄兒,阿豪啊!」 他歡喜若狂般緊抓我強而有力的臂彎,興奮道:「你真的是大哥的兒子嗎?來,我帶你去用午膳,去!」 哇!這傢伙真熱情。 於是祥叔叔領我坐古舊的公車前往北京著名的狗不理飯店。 在東歪西倒的公車上,他眼睛不規矩地上下打量我十數遍,其間夾雜曖昧的笑容。 他驀然「哼」了聲道:「你這小子真像你爹!」 祥叔叔剛一說話,便是那麼不客氣,給人真誠不渝的感覺。 我亂扯地胡鬧道:「你錯啦,我該比爹更帥,開玩笑。」 「開玩笑」這三個字是我國語裏最標準的發音。 「呀!」我不禁驚呼起來,因為祥叔叔拍了我大腿一記,然後他笑而不語。 我百無聊賴,找些話題問道:「聽你說,你、爺爺和現在住在北京的四合院,對嗎?」 他回應道:「原來你爹和姑姐也是在那裏住的……。那可是以前的事,待會定讓你拜見你爺爺。」 我裝出個誠懇的笑容,微笑道:「這個嘛……一定一定。」 不知怎地,祥叔臉上遂蒙上一層黑紗,頹廢地道,「你爹二十多歲便離開北京,因為相士說你爹生辰八字與父母完全相剋,結果你爺爺竟迷信到個不可理喻的地步,狠心趕走你爹;而你姑姐硬給迫婚,嫁了個有錢的上海男人。真不知道老人家是怎樣想的。某些中國的傳統禮法已不合時宜,他們卻盲目跟從,結果弄得整個家各散東西,很不愉快。」 我拍一拍他的虎背安慰道:「過去就讓它過去,當粉筆字抹去。」為免他再次動氣,我轉個話題問道:「喂!我的叔這麼帥,定有很多狂蜂浪蝶撲來?」 祥叔報以個苦澀的微笑道:「一個都沒有。」然後他把目光投向街景,一言不發。 都是我犯賤,挑起祥叔的傷心事。 於是我逕自聽我的鐳射唱碟。 「唧——」,公車停在狗不理飯店前。北風呼呼捲吹,寒風削骨。這裏只有攝氏一兩度,這麼大個子了,我終於理解到甚麼叫隆冬。 我跟叔叔的虎背,企鵝般的行姿,捏冰結的雙手鑽進飯店內。 狗不理飯店果真極具中國的建築特色,入門先是半米高的門檻,背後是一堵富有中國藝術雕花的木牆,端莊美觀。天花的橫樑縱橫交錯,但交接有序;暗黑的花燈下,飯店倍添中國的神秘美。 祥叔叔耐心介紹道:「看你的樣子肯定不知道狗不理飯店的由來?讓我在此拋一拋書包。咳──唔──,狗不理之所以叫狗不理,是因為開創者高貴先生的小名叫『狗不理』,最著名的是豬肉包子。豬肉是用上乘的家豬來造,配以特色醬料,而且師父更要拿捏火侯得宜,故特別好吃。」 「真捧,極品!」我訝然大呼。 包身軟如白雲,肉肥而不膩,肉香驅而不散,極具口感。 香港人的食品不是叉燒飯便是咖喱牛腩飯等沒有營養的快餐,根本忽略了本土中國的飲食文化——即用心地享受其食品的心思及帶來的滿足。 「爹!我在這裏。」一把清脆悅耳的少女聲自飯店門口直轟進廳內。 我的天!我根本不能相信我的眼睛。 一位清麗脫俗、肌膚白得發亮的少女站在門口。那少女五官與天使般的臉孔配合得天衣無縫:黑黑黛眉下有雙皎潔無暇的星眸;鳥黑的秀髮束於後枕,猶如一條小小的瀑布有意無意間跌墮於後頸。予人無比純真,不染塵俗的味道,與現在俗氣滿溢的少女相比,我的娘!真是天壤之別啊! 我看得圓瞪杏目,差點連口裏的包子也一併吐出來。 祥叔叔沾沾自喜介紹:「帥哥侄兒,她是我的寶貝女兒。」 那少女報以個鮮花盛綻的微笑道:「你好!我叫徐敏,喚我小敏也可。」 我腦袋立時爆出十萬個問號。第一,祥叔叔不是說過自己是獨身嗎?難道他靜悄悄的往外攪風攪雨,誕下私生女,但這個可能性不大,祥叔是個老忠厚,不會不會。第二,若果那少女真是他的私生女的話,理該姓黃…… 祥叔叔接結了賬,一屁股騎上國產三輪單車上,向我大呼道:「帥哥,結了賬了,還不快上車。」 我連忙翻上那國產三輪車後座,叔叔負責控車,徐敏和我面對面地坐。她的眼睛望我的眼睛,氣氛怪異。
我打破沉默道:「我全名叫黃豪賢,叫我豪哥也好,也可像你……爹一樣叫我做帥哥。」 她被我半咸半淡的「普通」話得花枝亂顫,俏臉泛起兩朵紅雲,美得不可方物。 她回復俏臉,正經地釋述:「北京人出入也踏自行車,自行車可說是人的一雙腿,沒有它出入也很不方便。所以你不難看見一又一的『自行車黨』在街上行走。」 我不住點頭,這北京小文化真有趣。 祥叔叔從袋裏掏了包香煙出來,緩緩燃點,遂吸了一口,呼出團煙圈。 吸煙——我想起了肺癌,肺癌──我想起了父親。 我向徐敏坦白訴說,直覺她是位可信的聆聽者:「母親自少離開我,爸吸煙得肺癌而死,這次回來是把爸的骨灰安葬於家鄉。」 她聽畢說話,俏臉微變,回應道:「我自少便是個孤兒,因為我父母認為女子不中用,沒有瓜分祖業的權利,幸得你叔,即我爹於東長安大街收留我,專責服侍你爺爺。」 我之前心內的疑團亦迎刃而解,「哦」了聲,表示明白。 中國傳統的社會講的是重男輕女,在這迂腐的思想下產生了無數個人、家庭及社會等悲劇,這些想法只是以前書本看了知了便算,現在我可體會其荼毒人生、可怕的滅能力。徐敏便是個好例子。 三輪自行車在叔叔駕輕就熟下,轉進熱鬧的王府井大街。 祥叔叔抽煙介紹:「在清朝時這裏有幾座王府和一口井,故稱王府井大街。全街長約一里,是北平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我們的四合院就座落於街尾。」 自行車穿過摩肩接踵的人潮,停在一所四合院前,地標正正寫—— 「王府井大街十三號」 四合院是方形的平面設計,其建築充份反映歷史工藝的遺。屋頂由青瓷磚一塊塊疊成;大門的樑柱由粗大的槐本所造成,經過長期的風化,槐木出現一道又一道的裂痕;地面則由扁平青麻石鋪成,上面偶爾長出一苔小青苔或小草;而屋簷朝天的四方翹起,有泰山壓頂、睥睨天下的味兒。 不禁使人驚嘆古中國偉大的建築。 我低吟道:「爹,你回家了!」 我是個走在社會尖端的青年;而古老的四合院卻是快要被社會淘汰的產物。兩者根本生存於兩極端、根本生存於不同的時空,大抵拉不上關係。 不過,父親的骨灰把我這個年青人與四合院建立了一種不可言諭的微妙關係。對我來說,它是個陌生東西,但又總覺得它散發令人熟悉的氣色,真奇怪!唯一解釋是我和它身上流黃家的血罷。 祥叔叔帶我穿過寬敞的天井,直抵大堂,並興奮地大呼:「爸媽,看我帶了甚麼人來?」 一位瘦如黑柴、滿臉皺紋、白髮蓬生的老頭兒安坐在酸枝大椅上,露出種希冀的目光;坐在他旁的是位年邁八十的老婆婆,雙目有神,嘴角綻出充滿盼望的微笑。 叔叔釋述道:「這是大哥的兒子,你的孫,是真的,快斟茶給爺爺。」 「哦」。我支吾地應了一聲。 面對爺爺,我倒沒有強烈的感覺,可能是我對他們並沒有深切的了解。若不是爸爸的遺願,我和這對老人家只不過是互不相識的陌路人。 頃刻間一隻炭黑的手按我的頭蓋,是爺爺!然後他雙手緩慢下滑,撫摸我的臉蛋。 我能清楚感受到他粗糙的手掌與我光滑皮膚磨擦得來的異感。然後他張開已下陷的嘴巴對我耳吟吟細語。 坦白說,他們講的是地道北京語,我根本一點也聽不懂,只是裝明白般不住點頭。 終於按耐不住淌下淚來,或者她從我身上聯想到早年遠去的父親,誰也沒想到父親竟一去不返,那麼快離開我們……包括祥叔叔、徐敏及爺爺都被傷感的氣氛感染,一起哭了出來,霎時間大堂裏充滿悲痛至極的傷感。 中國人確是看重鄉情的民族,所謂「生於斯、葬於斯」。他們對家鄉有濃烈的鄉土情懷,不像西方人般實行獨立主義,每個人與家庭、家鄉分離。中國人重鄉情的優點使人更形團結,人與人之間變得密切,這點已值得我們中國人感到自豪。 叔叔把爸爸的骨灰安葬於四合院的後園後,然後為我打點一切,安排南邊的廂房給我居住。 這天晚上,祥叔叔親自炮製了全鴨大餐來歡迎我這個「貴賓」。酒席上,爺爺吃了幾口飯,喝了幾口白玫瑰露酒,便回房休息。 叔叔右手轉酒杯,淡淡地道:「侄兒,你打算甚麼時候離開北京?」 徐敏秀眸一瞬間瞟了我一眼,露出個好奇的樣子。 我抓抓凌亂的頭髮,答道:「四天後吧!」 叔叔「唔」了一聲,沉思了半晌。 徐敏雙手拍一拍大腿,然後站立道:「爸、豪哥,明天要返大學上音樂課,我先回房休息,你倆叔侄慢談,失陪了。」 我收回對徐敏依依不捨的目光,然後說聲「晚安」。 一個明月皎潔、花氣四溢的晚上,廣闊的天井裏,剩下我倆叔侄坐在飯桌旁。 當我仍回味著徐敏清麗絕倫的粉背時,祥叔叔倏地橫伸右手放在我的寬肩上,把我從夢幻般的仙景抽離,重投現實。 他帶點醉意道:「你爹二十三歲便離開這四合院。當年有個臭相士說你爹八字與他老豆老母相剋,若不離開北京的話,便闔家完蛋!哇哈,開玩笑。」 祥叔遂將目光投往無邊夜空,緬懷過去道:「我還清楚記得你爹、姑姐和我小時候最愛在這天井捉迷藏、猜拳的。那是我三兄妹最快樂的童年,負方便請勝方吃冰糖葫蘆。告訴你一個小秘密,你哥常拉我串通來騙你姑姐,結果你姑姐就哈哈……」 他旋又呼一團淡白暖氣,喋喋不休說:「可是這一切都是以前的事……帥哥,你聽了我說這麼多廢話,不覺得悶蛋嗎?」 其實我當作是聽別人的故事罷了。 我聳一聳肩,表示不介意。我開始喜歡與我叔叔相處,他就像爹,我就像他的哥哥,我們好像父子也像兄弟,多麼親切啊! 我終忍不往好奇,藉叔叔喝醉單刀直入問道:「叔,你可快到五十大關了,怎麼半個妞兒也弄不上手?」 祥叔叔醉薰薰答道:「我愛的人,她不愛我。我不愛的人,她總纏我。就算雙方有意。又怎樣?八字不夾、家世相差,故父母反對。小子!又在套我的秘密。沒了!我看來是個天生愛情失敗者。」 我不禁搖頭嘆息,深深同情叔叔的遭遇。 哼!又是迂腐的禮法在攪鬼,祥叔你確是個愛情倒霉者。 祥叔回報苦澀的微笑,然後伸手往內袋掏去。 我猛一錯愕,大呼道:「叔,抽少支煙好嗎?你都知道我爹是因為患上……。」 半晌後,他收回往內袋掏的右手,站起來收拾碗筷。 在寂靜無聲、暗黑的提燈照射下,我和祥叔一起把碗碟洗淨,忙到夜深才倒頭大睡。 二零零二年二月九日——晴天。 我睜開沉重的眼皮,望一望手錶。啊!是正午十二時正,我定是很累了。 我梳洗過後,踏出房門便瞧見祥叔叔。 他當頭便語帶諷刺「早安」一句,提議說:「來,肚子餓吧。跟我來,我帶你去吃好東西。」 我沒頭沒腦跟他的虎背,他的氣質及型格真像我死鬼爹,不同的是他是位好爸爸。 祥叔懷著懷疑的眼光質問:「你懂踏自行車嗎?」 對。我當然懂得,以我好勝的性格,誇張地吹牛皮道:「你可知論踏單車,黃金寶也要在我車尾吃塵,開玩笑!」 然後我和他競賽般一口氣走了半小時,來到東長安大街。 叔叔終鬥不過我這個連「阿寶」也吃塵的青年,豎起姆指讚賞。哈,竟不知醜來挑戰我,簡直是自取其辱。 我得意地笑道:「老人家不要太拚命,弄傷了可真不是『開玩笑』。」 他圓瞪怒目,旋又搖頭嘆息道:「你這傢伙真像你爹,都愛自吹自擂!」 我從沒想過在北京踏單車是那麼有趣刺激的一回事,不踏單車的人被視作怪人,漸漸地踏單車已成為一種特色的地道文化。 祥叔領我往路邊的食店,請我吃著名的刀削麵。只見師父在麵糰頂上,兩手拿菜刀左右開弓,從頭的左右兩側交互把麵削進沸騰的湯渦裏,頗具民間小食特色。 在用膳過程中,叔叔道出在這東長安大街拾徐敏的情況,結賬後帶我加入北京下班一族的自行車隊裏去。 你很難想像成千上萬的自行車一併在地上行走的壯觀情境,它們走得緩慢整齊、不會爭相爬頭,極具秩序。 我和叔叔踏自行車遊覽附近一帶的名勝,如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景山公園等。 不知不覺,現在已經晚上七時半了,可能北京位處北方,加上是隆冬關係,天已全黑。 祥叔叔於東風巿場買了菜後,對我說:「帥哥,我現在可要回四合院弄晚飯,麻煩你幫個忙往北京大學接小敏回來好嗎?拜託。」 是了!差點忘記徐敏今天往大學上音樂課,我一口答應了。 經祥叔指明大學位置後,他便逕自返家。我踏著自行車朝大學駛去。 「呼——呼——」,北風入夜後進入瘋狂的狀態,劇凍非常,硬要把我活活凍死——因為我在這裏苦等了兩小時。 「可惡!身為老師也不守時,這些是甚麼的鬼老師,我的娘!我快要凍僵了。祥叔叔,你可害得我苦了!」我不忿地自言自語。 在暗黑的燈光下,一道人影姍姍走來,那不是徐敏還有誰? 她垂下螓首,抿櫻桃的小紅唇,頹廢地在我身前經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