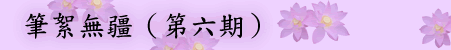阮邦耀校長 今年,百多盆白色的百合花開得很早,三月底的天台上,部份花兒已按捺不住,率先露出清秀的臉龐,親親地展示他們的驕恣。四月初,它們遍佈校園,爭取分秒,意圖吸引每位員生的目光,散發璀璨而短暫的魅力。可惜,它們最燦爛的時刻,適值是復活節假期,到四月廿八日的校園建設日,卻已屆垂暮,不能參加慶典,被搬回天台去了。培育它們的謝先生指出,每株枯萎百合花的根部會長出大小不等的種子,來年百合花的大小將取決於種子的大小。今天,它們仍在那裏默默地汲取著天地精華,為下一代創造最有利的先天條件。 謝先生說,培植百合花最容易不過,只需在合適的時候將種子植入泥中,定時灌溉,無需除蟲,無需除草,它們便可以長得很好了,花謝後只要放回天台上,稍後便可收集種子,如果情況理想,下一年的收成更可增多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我聽見後的思想反射是:真的簡單到連我也可培植出這許多壯健的百合花?甚麼是合適時候?種子應植入泥裏多深才有利生長?灑水過多會否影響百合花生長?真可悲,只怪自己的科學思維中毒過深,遇到不懂的問題,便直觀地追溯、求真,錯過了不少享受從美與善兩個角度看事物的機會和時刻,幸好尚保存了半分的醒覺性和自省能力,這直觀思想過後,腦裏浮現的是一幅幅歡愉的動態圖象 ── 退休後我夫婦倆每年在花園裡培植出數以百計的百合花,分批送出,令子女和朋友們家裡都增添一分幽雅和清香 ── 真盼望有這一天。有了這欣喜的感覺,便特別留心聽謝先生的講解,也不教他感到對牛彈琴。 在百合花盛放的日子裏,我實在很喜歡在黃昏時漫步校務處門外長廊,清風過處,百合花一齊列隊敬禮,靜靜地飄送那獨特的幽香,為我疲憊的腦袋按按摩、為拉得緊緊的血管舒舒壓。百合花擁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和生命循環,它與校園同時並放的蘭花、海棠、桂花、太陽花等十分不同。它們整個隊伍差不多同時進駐校園,在個多月的璀璨過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可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它的璀璨不因其他花朵的精采而有任何增減,它的枯寂亦不因其他花朵的繼續開放而帶半分猶豫,甘願默默地、歇力地奉獻自己以作傳承,這便是人類安身立命的要義所在,正如《中庸》所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百合花在校園璀璨盛放是培植者的知識、經驗和不懈努力的成果。教育亦是培育。教育實踐長期以來徘徊於慣性操練與自由發展的兩極連線上,找不到平衡點,事實上,不單田中的同事們在討論教育課題時常陷入這兩極化的爭論之中,中、西方的教育實踐亦可概略地被界定為各走一端 ── 東方式慣性操練的體制能有效地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但局限了學生的思維和多元發展;西方則著重自由發展的體制,它有效地培育學生的靈活思考和均衡發展,但卻嫌學生所獲取的硬知識不足,令到遇事時欠缺整全和深度的聯想。在目前,兩方的陣形均有向連線中位找尋平衡點的趨勢。據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所得,對於尖子學生來說,無論在東方或西方,均具備高度的自控能力,能持續不息地自我學習,個人可在學業、音樂和體育等多方面取得平衡發展,包括具備靈活多變的思維。 田中百合花的生長,充滿著適時和自然之道,可對田中的教育方式帶來一點啟示。道不遠人,人之為道遠人,《詩經.豳風.伐柯》有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正帶出這個道理。
|